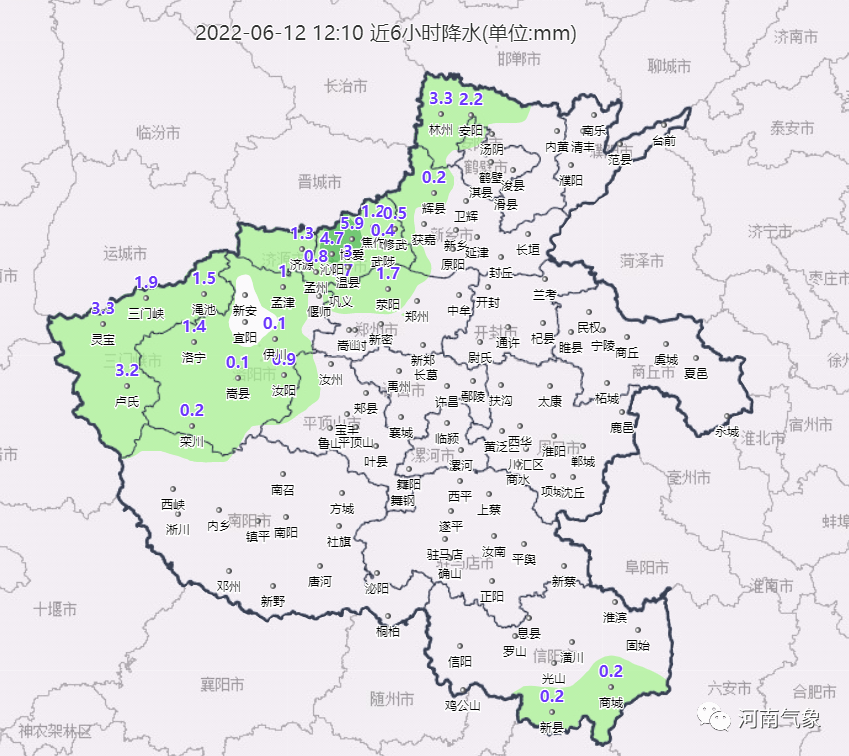【明日方舟:第三方干预局】[拉普兰德篇:法兰克的宝藏] 第十四章 生活
“姐......切利......呃......”
“叫我德克萨斯就行。”
“好的,德克萨斯小姐,我......”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“你现在......”
“哦,不,你先......”
“你先说吧。”
“好。”
埃托雷抿了抿嘴,拿起桌上的一杯冰水,一口灌下去,然后“砰”地把厚实的玻璃杯礅到圆木桌子上。
昨天,他洗了十几年来的第一个热水澡,还换上了一套罗德岛的干净衣服。他的头发也终于不再灰不溜秋,呈现和德克萨斯一样的黑蓝色。
站点主任站在休息室门外,靠在沾满油污和锈迹的门框边上,用余光瞟着这有些违和感的一对组合,却又不敢接近。
埃托雷又犹豫了一会儿,才开口说话。
“我这么讲话没问题吧?”
“怎么了?”
“唔,我说话可能比较糙,不懂得该怎么和你们交流。”
“没有这回事,你维持原来的说话方式就行。”
“那样就好,否则我就得端着了。我和维罗娜说就得端着,那样可是很难受的。”
“你要说什么?”
“那个,萨卢佐小姐她......她怎么样啊?”
“她正在养伤。伤的怎么样?按她自己的话来说,没死就行。”
“我把她弄成那样,真对不起。她肯定很难受吧。”
“她可能并不在乎这件事。”
“真是大人大量。”
“大概不是大人大量。”
“不是这样吗?”
“我也说不清,但她的想法和别人都不太一样。而且你也不在岛上,不会和她有什么冲突了。”
“谢谢你们,德克萨斯,能给我这个机会。”
“博士并不同意你上岛,但拉普兰德极力挽留你,再经过凯尔希女士同意,这才想出一个妥协的办法,让你当驻外干员。他已经做出让步了,你要理解这点。”
“我晓得,一个杀人犯没那么好让别人相信。但是你刚才说什么,萨卢佐小姐她!”
埃托雷反应过来之后,瞪大了眼睛。
“嗯,可以说是她给你的这个机会。”
“真想不到,真想不到......什么人会帮要杀自己的人呢?”
“我猜她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想帮你。这也是她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之一——她从来不会真的记仇。”
“她不会是想和我较量吧。”
“我不知道她的想法。”
“希望不是真的想较量。算了,不管怎么说,我这辈子欠她的。而且,我现在也没脸和萨卢佐小姐在一块儿工作,这样安排是最好的。”
“理解就好,具体的就留给你自己思考。”
“可我还是想感谢你。”
“感谢我?感谢我什么?”
“也少不了你在其中说道,不是吗?你了解叙拉古,还是德克萨斯家真正的大小姐,他们肯定得听你的话。”
“我也发表了意见,但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并不大,毕竟我代表的家族已经消失了。”
“消失又怎么样呢,对我来说它也没存在过。我就认得你一个人,胜过认识整个家族。”
“这也是个问题。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你。”
“面对还不简单咧,咱俩现在不是在面对面吗?”
德克萨斯苦笑一声,用吸管嘬了口冰水。
“呵呵,能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我是说,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,可我又从来都没见过你。这种感觉......很......”
“很别扭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这么一说,我也感觉蛮别扭的。按你的话说,我很小就被送走了,德克萨斯家族对我来说就是个传说而已。现在我自己却突然成了一个德克萨斯,跟做梦似的。”
“我想现在,我们最好以同事论处。”
“当然,你觉得合适就行。哦,再问一下,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来着?”
“长期驻外干员,职责是维持罗德岛、西西里夫人和法兰克外来人口的关系。”
“啊,对对,你瞧我这记性。挺高大上。”
“这是个相当模糊的职责,需要你自己思考该做什么。”
“是啊,现在法官大人死了,维罗娜那家伙也跑了,整个法兰克上层乱成了一锅粥。我一直以为,给她做事就是给西西里夫人做事呢。她说,做完这票就给我钱,让我去过普通人的日子,结果......也许我该去蹲大牢。”
“这不是你的问题。”
“唉,话是这么说,可我不知道弄死了多少没犯错的可怜家伙。那毕竟都是大活人啊。”
“你说的没错,前杀手应当永远记住这点。”
“我会的。”
“不过,你也是个很古怪的人。”
“古怪?怎么说?”
“我以前见过的杀手很难这么快就转变思路,去同情自己以前的目标。甚至......他们都不像你这样说话。”
“咋说话?”
“只是正常的交流,他们都做不到。”
“你是说那种走在街上都阴森森,一看就很不好惹的杀手?”
“嗯。”
“我和他们不一样啦。开始接触搬运工的时候,我还只是模仿而已,平时也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到了后来,在他们中间呆久了,我也就成了如假包换的一员。我还会向往一下那种生活,这不就被骗了吗。”
埃托雷说着,看向休息室的窗外。法兰克的头脑被斩去了,站点的搬运工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照常搬运着那些沉重的货物。在这个喧嚣的场景里,他能认出一些熟悉的身影。
“到现在了,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讲。”
“你指哪方面?”
“所有的这些事。我没法解释,为啥我突然就和官家扯上关系,又负责保护他们这些法兰克的‘外人’的权益。”
“如果你实在说不清,告诉他们事实就行。”
“你确定吗?未遂政变,猎狼人,黄金权杖......事实听着像假的一样。哈,看我现在的身份——另一个德克萨斯——我自己都觉得像假的。”
“事实的优势就在于,它是真实的。不管看起来多离奇,最后总能说通。”
“你不会是说,我得告诉他们我是个刽子手吧?”
“我没有要你和盘托出,说你想说的那部分就行。‘事实’不等于‘真相’。”
“好吧,看来我得想想,怎么弄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真相了。”
德克萨斯微微一笑,从胸袋里掏出银色的怀表,按开表盖看了一眼。
埃托雷看到她这个动作,一转头,发现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已经站在休息室门口了。经理识相地挤了出去。
还没等二人说什么,他们便一股脑涌了进来,依靠在脆弱的墙板和小桌子上,把它们弄得嘎吱响。几个不一样形状的大头围在埃托雷身边,吐着不同味道的口气,七嘴八舌地说这说那。
“埃托雷,你发达了啊!”
“听说你找到了黄金全掌......”
“放屁,是黄金棒槌!”
“维罗娜真被你打跑了?”
“别吵,一个一个说!”
“究竟长什么样啊!”
“萨卢佐家的人真是白色毛发的?”
“他们有啥了不起?要多少有多少。这儿可有个正儿八经的德克萨斯,看这头发!”
“以前可不知道你还会打架。让我看看你的武器!”
“从你的嘴里吐不出珍珠来。”
“我就跟你说,这家伙会有出息的......”
也许是传达中出了差错,这些话有很大一部分是瞎扯。但埃托雷暗自想到,现在流传的这个版本的故事,可能比真实的版本更能让人接受,甚至都不需要他自己去编造。
就好像有人帮他把瞎话都说了一样。
“*阿卡胡拉粗口*,让我先说!”
罗恩的阿达克利斯长嘴从人堆的缝隙里伸出来,吐出一连串脏字,这才把其他声音压下去。他轻咳了两声,挠挠坑坑洼洼的脑瓜顶,和自己的小伙伴四目相对。
“唉,我是想说点什么,但该怎么说呢......”
“你好?”
“你好......你怎么样?”
“我很好啊。”
“很好吗,那就好。”
一阵沉默。旁边的一个菲林不乐意了,插嘴进来。
“你不说让我说!”
“闭嘴,古塔,你一开口就没完!”
“真无聊。”
“我想想。哎对,现在是属于哪个什么岛?”
“罗德岛。”
“德克萨斯小姐跟我说过,好像是个好心眼的公司。你去过,真是这样吗?”
“我很难说怎么样。不过岛上一半都是感染者,要不是好心眼,这样的公司恐怕开不下去吧。”
“有点道理,我觉得我可以相信他们,能考虑我们这些穷人。”
“我也觉得他们可以。在和法兰克的贸易条款里,他们把外来户的条款写进去了。”
“是吗,这么好。不过维罗娜不是已经跑了吗,他们和谁签的条款?”
“谁知道呢。”
“哼,还得看以后有没有效果,能不能真给我们落实身份之类的。你晓得,我遇到过好些说的好听的,到时候就是收完钱跑路,都是一群缺德玩意儿。不过我猜有你担保,应该可以信这个罗德岛。”
“他们以前做过很多类似的事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“完啦?”
“完啦。”
“我不觉得你就这么点儿话要说。”
“就是这些。”
“你不打听一下我的故事?”
“那个嘛,以后可以慢慢说。不过现在......嗯......”
一向大大咧咧的罗恩突然扭捏起来,用尖利的爪子扣起了自己长满鳞片的手背,在黑色的角质上扣出几道白印。相比平时,那爪子洗的颇干净。虽然还留着一些顽固的油污,但镶嵌在鳞片缝隙里的黑泥巴都没了。
休息室的空调是坏的,再加上一群热气腾腾的汉子,里面愈加闷热。玻璃杯里的冰块早就化成了水,水面跟着桌子一起晃悠着。
感到背后无数双戏谑的眼睛看过来,罗恩终于顶不住了,大声地吼了出来。
“让我摸一下你的头发!”
一阵尴尬的沉默。然后是几乎冲破站点穹顶的哄堂大笑。
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!”
“跟个小娘们似的,害不害臊?”
“你自己的话,你就自己说去。”
“这个‘领袖’......”
“怎,怎么回事?”埃托雷看看罗恩,又看看人群,茫然无措地问道。
有个丰蹄挤过来,带头和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解释。
“你还不知道吧,埃托雷。这家伙......”
“他可喜欢那些传说了!”
“他整天一副埋头干活啥都不知道的样子,其实比谁心思都花。”
“就是装正经。”
“这蜥蜴可最喜欢德克萨斯的故事!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识字,跑到图书馆里去了。”
“得了吧,他根本就不识字。”
“听人讲的故事,不行啊!”罗恩小声抗议道。
“听故事你眼睛都发金光,要真见到一个,还不腿发软。”
“你知道不,他见到罗德岛那个黑蓝色头发的姑娘,两眼都离不开啦。”
“我们开始都以为,他看上人家了......”
“这死心眼子还没看上过姑娘呢。”
“你猜怎么着,他就是想摸一下德克萨斯家族的头发。但人家是姑娘,他不好意思开口。”
“所以,你就找上我了?”
埃托雷听完这一串愚蠢的宣讲,马上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。但他随即又收回去,把头扭过来,伸向罗恩。
“怪恶心的。就这么一次啊。下次你找到姑娘,摸她的头发去,老子不奉陪。”
他闭上眼睛,撅起一张狼嘴,调侃着说。
罗恩咳嗽了两声,赶在这短暂的沉默结束之前赶快把爪子伸过去,捻了两下那已然干净了的头发,再触电似的抽回来。
一个人猛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背,他一下子朝前倾倒过去,重重地撑在桌边。大家随即又笑起来,一边嘲讽着他们可怜的“领袖”,一边胡乱地唱起一些难听的小调。
埃托雷也跟他们笑,笑了很久。然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,环顾四周,发现朋友们嘴里的,那另一匹蓝发的孤狼,早就悄无声息地离去了。
这很不寻常。如果他没记错,这是来到法兰克以来第一次,自己未能察觉到一个人的——而且是一个曾经作为自己对手的人的——气息的消失。
他不再咧嘴大笑,而是收敛地微笑着,仔细琢磨起这个事实的含义。
至少在这一刻,他完全放下了刺客警惕的本能,转而去体会自己早已熟悉,却又完全陌生的,名为“生活”的东西。
【明日方舟:第三方干预局】[拉普兰德篇:法兰克的宝藏] 第十四章 生活
“姐 切利 呃 ”“叫我德克萨斯就行。”“好的,德克萨
2023-08-26做梦吓醒预示什么(做梦吓醒预示什么 梦见吓醒是什么意思)
1、做梦吓醒,乃是在生活中有情绪不稳之故,得此梦者多有,生活中人情
2023-08-26联合国粮农组织:苏丹约2000万人口面临严峻粮食安全问题
当地时间8月25日,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,苏丹当前有大约2000万人
2023-08-26丹尼-格林:如果必须卖掉一个冠军戒指,我会卖掉湖人那个
丹尼-格林:如果必须卖掉一个冠军戒指,我会卖掉湖人那个,湖人,科比,马
2023-08-26又是别人家的公司!团建每人发3500元旅游基金
近日,长沙一公司给员工发3500元旅游基金一事登上热搜,不少网友表示十
2023-08-26又一大IPO来袭!美国最大在线杂货配送公司Instacart(CART.US)提交美股上市申请
智通财经APP获悉,当地时间周五,美国最大的在线杂货配送公司Instacart
2023-08-26
苏炳添、谢震业入围尤金世锦赛参赛资格 巩立姣冲击3连冠
2022-07-10
未来3个月 U21国足将与克罗地亚乙级队进行热身
2022-07-10
行走河南·读懂中国|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场活动进行
2022-07-05